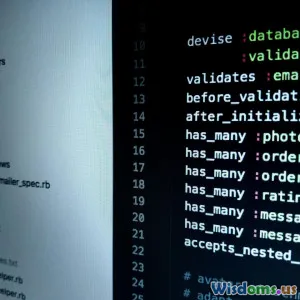为什么有些国家会随着时间改变官方语言
(Why Do Some Countries Change Their Official Languages Over Time)
2 分钟 阅读 探讨历史上各国官方语言变更背后的原因及其影响。 (0 评论)
为什么有些国家随时间改变官方语言?
当我们设想一个国家时,往往会将其与一种特定语言联系起来——如西班牙的西班牙语、泰国的泰语,或芬兰的芬兰语。But language, like borders and governments, can change. 在现代史上,许多国家的官方语言都发生了变化——不仅仅因为语言自身的演变,常常也是领导层或民众有意识的选择的结果。这些戏剧性的转折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从此类政策的涟漪效应中我们又能学到什么?答案讲述身份、权力与韧性的故事。
推动语言变化的历史力量

语言政策并非凭空而来。政治动荡和历史事件会极大地塑造一个国家被承认的官方语言。
殖民主义留下的语言印记仍在:
殖民强权往往将自己的语言强加于他们控制的土地。英语、法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成为官方或主导语言,在从西非到东南亚再到美洲的多样世界中,通过行政管理、教育和商业巩固。
在许多前殖民地,独立运动重新审视语言政策。
例子: 1947年独立后,印度将英语作为关键的行政和教育语言继承下来。然而,在民族主义情绪的驱动下,印度也推动印地语——在1950年宪法中宣布其为官方语言。尽管如此,英语依然保留了共官方语言的地位,这既体现了前殖民统治的持久影响,也揭示了多元文化治理的现实。
国家建设与身份认同:
渴望确立独特身份的新兴国家有时会舍弃外来或被强加的语言,以重振本土语言。
以尼雷尔在1960年代统治下的坦桑尼亚为例:尽管许多坦桑尼亚人讲区域性语言,尼雷尔确立斯瓦西里语作为统一的官方语言,以促进后殖民时期的身份认同与社会凝聚力,使国家与英语的殖民遗产保持距离。
革命与政权更迭:
剧烈的政治变动也可能促使语言变更。
在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等后苏联国家,摆脱苏联不仅是政治上的重新定位,也意味着语言上的重新取向。
拉脱维亚语在1991年独立后迅速重新获得官方地位,部分原因是为了重振被压抑的民族文化,并使其与数十年的俄化区分开来。
语言变迁背后的社会政治动机

每一项官方语言政策背后都错综复杂地嵌套着社会政治动机,涵盖从国家团结到地缘政治再到妥协。
统一一个支离破碎的国家:
在语言与方言错综复杂的国家,领导层可能推动使用单一语言以弥合社会或族群的分歧。
印度尼西亚,作为群岛国家,极其多样,独立后采用印尼语——一种改良的马来语变体,母语使用者很少,但作为第二语言易于学习。
其理念在于避免偏袒诸如爪哇语等占主导地位的本地语言,而是建立一个包容性的国家身份。
少数群体的包容与排斥:
语言政策也同样可能排斥边缘化群体。
南斯拉夫解体后,波黑、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以不同方式将彼此密切相关的语言(波斯尼亚语、克罗地亚语、塞尔维亚语)确认为官方语言,这不仅反映语言偏好,也体现新战后国家身份的形成。
然而,少数群体有时为了获得承认而斗争:例如中欧的罗姆人和塞浦路斯的土耳其语使用者,多年来一直为语言权利而斗争。
要点示例: 南非在显著的对比中,通过承认11种官方语言来实现和解与多元化,表明对其多元文化遗产的尊重,并旨在消除几代人的语言歧视。
政治信号与国际关系:
有时语言变更本身就是一种外交工具。
例如,卢旺达在2008年将教育的官方语言从法语改为英语,寻求与东非共同体和英联邦之间更紧密的经济与政治联系,并作为摆脱在大屠杀前政治中受到法语支持精英影响的遗产的一步。
平衡语言传统的挑战

在传统语言的怀旧与自豪感、实际可行性以及外交考量之间取得平衡,仍然是语言政策中最棘手的方面之一。
传统与现代性:
对于一些国家而言,重新确立历史语言是重获文化自豪感的途径。
爱尔兰通过几十年的努力,通过教育、媒体和公共政策等途径复兴爱尔兰语(盖尔语)成为充满活力的官方语言,这反映了在英语主导的环境下抵御语言侵蚀的持续努力。
然而,实际采用往往滞后,显示出语言一旦势头转向另一方就有多难重新振兴。
语言消失的风险:
选择优先一种官方语言往往会让少数语言处于风险之中。
在美洲、澳大利亚和非洲,随着政府推动与权力或经济机会相关的官方语言,数不胜数的原住民语言已经消失或濒危。
秘鲁的克丘亚语言案例——在1975年获得官方地位,随后又回退以偏向西班牙语——凸显了这种来回摇摆的斗争。
教育与媒体的双刃剑:
一个国家的教育和媒体体系可能推动所选官方语言的传播,往往以地方方言的消退为代价。
以突尼斯为例,独立后经历了显著的阿拉伯化进程,逐步用阿拉伯语取代教育和行政中的法语。
然而,许多城市精英仍然精通法语,以便参与全球交流与商业。
经济、教育与技术因素

官方语言的选择并不总是只是关乎国家认同。
经济因素、教育目标和科技进步深刻影响着哪种语言成为主导语言。
吸引全球商务:
英语作为国际商务、技术与科学的语言,施加着强大的压力。
在卢旺达等国,从法语转向英语的举措,部分原因是需要参与东非共同市场并与英语投资者建立伙伴关系。
为发展而标准化教育:
改变官方语言常被视为实现教育机会平等和提升识字率的方式。
在哈萨克斯坦,例如,为哈萨克语采用拉丁字母(取代西里尔字母)旨在让国家更紧密地融入全球网络并实现教育平台的现代化。
数字化与连通性需求:
科技进一步使语言政策变得复杂。
为实现数字化转型而努力的国家可能需要与在互联网上占主导地位的语言保持一致。
英语与中文在网上占据主导地位,掩盖了其他语言,促使全球年轻人要么支持、要么挑战官方规范,以适应数字通信的现实。
应如何驾驭这些复杂性:我们能学到什么?

对于考虑调整语言政策的国家,这条路充满机遇与风险。
从过去与现在的辩论中,可以得到哪些启示?
在务实与包容之间取得平衡:
官方语言不仅应体现历史或文化愿望,还应满足实际的沟通需求与社区生活的现实。
最成功的政策在语言的象征重量与社会经济和外交考量之间取得平衡——例如,新加坡承认四种官方语言(英语、普通话、马来语、泰米尔语),在公共生活中各自承担不同的职能。
避免政策陷阱:
自上而下强行规定一种语言——如果没有公众的认同——通常会导致摩擦。
斯里兰卡独立后优先承认僧伽罗语的官方政策激化了与泰米尔少数群体的分歧,最终导致数十年的冲突。
真正的与利益相关者对话、分阶段或多元政策方法往往具有更高的合法性和成功率。
多语能力的价值:
语言变动并不一定意味着抹去较旧的语言。
加拿大同时承认英语和法语为官方语言,并推动土著语言的振兴,成为在一个日益重视文化权利与多样性的时代的多元主义典范。
语言政策的人类影响

官方语言政策的变动深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机会、身份认同与归属感。
个人层面的问题:
当玻利维亚在2009年宪法中确立三十七种官方语言以承认土著遗产时,给部分民众带来了新的自豪感和合法性,同时也对行政实施提出了严峻挑战。
个人与社区的故事在适应新的语言环境时,既揭示了赋权,也揭示了挫折,成功取决于对教师培训、资源开发和地方倡导的投入。
代际传递:
在政策变革时代成长的儿童往往成为祖辈单语亲属与日益变化的社会之间的事实翻译者。
虽然官方语言的采用可以打开通往更广阔世界的大门,但也可能在无意中侵蚀口头传统、民间知识以及被威胁语言承载的独特世界观。
全球现实:
全球互联互通加剧了这些挑战与机会。
侨民、移民和国际学生经常在语言多样的拼合环境中建立生活。
能够让公民具备强大的多语言能力,同时不牺牲文化根源的国家,在经济灵活性和社会和谐方面都将受益。
平滑、稳定的官方语言政策调整可以帮助国家为自己书写新的故事,同时尊重既有的历史。
但这样的变革从来不仅仅关乎语言本身:它们反映并塑造着一个民族对自身以及对世界的本质。